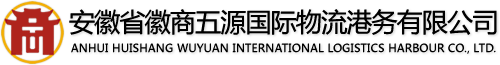逐梦大运河,新时代水运正在构建
“多年来,大量有关大运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地位和现代意义提供了丰富材料。但是,大运河的主要功能还是交通运输……”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日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做客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讲座,带领大家解读多元视角下的大运河。
贯通南北,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
正如贺云翱所言,历史证明,人类的文明创造活动离不开自然的支撑和规约,但是人类也可以通过大型工程对自然特别是河流水系进行改善和重组,创造更优化的文明生存条件。
列入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而更具广泛意义的“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成为支撑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自建设之初,就具有连通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作用,服务于国家政治中心和国土统一。”在贺云翱看来,大运河的独特价值首先就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中国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淮河等无不如此。东西走向的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运动空间。但它也有缺点,从三国时期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再到五代十国,南宋,几乎都以淮河—长江为界,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所以,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融通各自然大河的水上大通道。”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城(今江苏扬州附近)引江水北行至末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后来还沟通济水与黄河,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大运河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时期,连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曹操建立起河北平原水运网络。隋唐时期,大运河连接了关中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实现了“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的重大作用。
“南北贯通,而且是连接包括海洋及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贺云翱认为,大运河的伟大创造性,就在于它重构了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成为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
通江达海,物流体系早已实现四通八达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南北交通运输,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中国大运河的起点在哪?它于何时诞生?就全面认识大运河的运输网络体系而言,贺云翱另有自己的看法。
贺云翱认为,最早开凿的运河当数春秋时期楚国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支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来伍子胥率吴国军队伐楚,曾疏浚此河,故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
春秋后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为攻越、征楚、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越国也开凿了浙东运河最早的一段,由绍兴至上虞,又名“山阴故道”。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附近),城下凿河,引长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邗沟通常被认为是大运河的“逻辑起点”。
公元前482年,吴人又从菏泽引济水入泗水,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这样,长江、淮河、济水、黄河几大水系就连为了一体。到了战国时候,魏国开凿鸿沟,自此邗沟、菏水、鸿沟等局域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的区域性运河体系。
连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灵渠”,始建于公元前214年,由秦始皇下令修建,全长仅37公里,却通过贯通湘漓两江,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贯通,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
此外,大运河同时还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大小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了一个大国四通八达的物流体系。可以说,大运河连通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先后形成的三条主要通道,即“绿洲丝路”“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展现了它开放、流通、融汇的功能特性。
通古达今,中国水运走向复兴时代
近20年来,中国在大运河考古方面取得的丰硕成就,正让大运河这个异常复杂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呈现于世人面前。
大运河考古涉及工程、地理、地貌、水文、水利、环境、交通、运输、城市、乡村、手工业、农业、商业、建筑、艺术、饮食、人物、中外交流等许多领域:隋唐大运河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北1200米处,展示了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隋唐大运河含嘉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为研究隋唐大运河与东都的关系及中国古代地下粮窖结构和储粮方法,以及研究隋唐时期对粮仓的管理制度、漕运情况和农业经济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镇江先后发现了宋元时期大运河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和元代大运河遗址,提示着运河、石桥、仓储与长江四者有机融为一体……
贺云翱表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运河作为黄金水道,承担着水运的主力军,支撑起了多个王朝的漕运命脉。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北宋沿用隋代的运河系统,经大运河向当时首都提供的漕粮每年有六百多万石,最高能达到八百万石。明宣德年间,经大运河运送首都的漕粮最高时达到近七百万石,并自明成化年间起,正式规定漕运总额为每年四百万石。该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
除了漕粮,大运河堪称当时的水上“高铁”,也是其他货物的运输通道,包括木材,以及建造房屋必需的砖石,还有丝绸、工艺品等。比如明清时期,产自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中的珍贵名木,经过砍伐、运输到山沟,再编成木筏,等待雨季涨水时推入长江,再沿运北上,送到北京作为建筑材料。所以,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明清紫禁城是从大运河上“漂来的一座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古人充分利用了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运道相结合,这就使得大运河所处历史空间与我国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带、淮河生态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一带一路”交汇地等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今天,基于水运具有惊人的、不可替代的重大经济作用,人们开始对传统水运重新审视。据贺云翱透露,全国目前有十多条运河已经处于规划、论证或部分建设当中,比如安徽境内“江淮运河”的开通,它改变了淮河中上游地区与长江中上游地区之间水运要绕道京杭大运河的状况,可缩短200公里至600公里航程。预计到2030年,江淮运河水运量将达2亿吨。已经在建设中的还有安徽至上海的“芜申运河”,这是一条春秋时期的古老运河,以位于南京东南部的胥河为重要航段,将连接水阳江和太湖两大水系,它的重新修建,不仅为长江提供又一条辅助运输水道,而且可直接服务于长三角南部区域。
据贺云翱介绍,交通运输部此前曾印发《内河航运发展纲要》,目标是到2035年,内河千吨级航道达到2.5万公里,内河货物周转量占全社会比重达到9%,重要航段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45分钟,主要港口(区)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30分钟。中国将由此迎来一个新的水运时代。